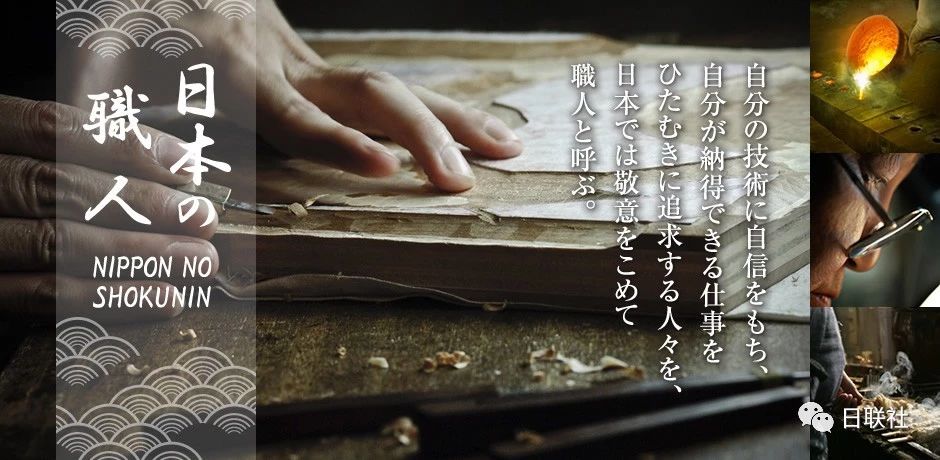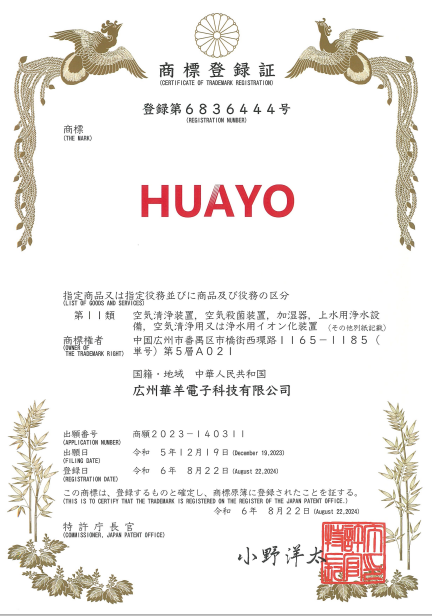剛剛獲獎的本庶佑是第26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也是第5位獲得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的日本人。日本超過了德國、英國、法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諾獎大戶”,其中23個為自然科學獎。
日本人連年斬獲諾獎,離不開日本政府對基礎研究長期穩(wěn)定的支持。早在1995年,日本國會就通過了《科學技術基本法》,其后制定了多個5年計劃;去年1月,日本內(nèi)閣審議通過了《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6—2020)》。該計劃提出,未來10年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適宜創(chuàng)新的國家”。
日本人還有令人敬佩的“工匠精神”。所謂“工匠精神”,就是一輩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將這件事做到極致。跟日本人的“工匠精神”不同,中國人崇尚的是善變的“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總是希望走捷徑、抄近道,而不屑于“扎硬寨、打硬仗”。
一萬元日幣上印著的福澤諭吉,他是日本明治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貨幣上印上科學家和文學家的頭像,是日本的傳統(tǒng)。
還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大多有著相對美好的童年,喜歡親近自然、探索自然,喜歡閱讀、善于閱讀,而且父母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啟蒙和引導角色。
日本人屢屢獲得諾獎的背后,他們的教育和科研有哪些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地方?
“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chǎn)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2016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大隅良典說。
從小,大隅良典非常喜歡自然,采集昆蟲是一大愛好,他還是小學科學教材的編撰者。在他看來,讓小孩子們愛上自然、愛上科學,對世界抱有寶貴的好奇心,是一切的起點。
“(小時候)熱衷于飛機模型、半導體收音機的制作,夏天喜歡在小河里撈魚、捕螢火蟲、采集昆蟲,手持網(wǎng)子在野外一走就是一天。采筑紫、野芹菜、木通、楊梅、野草莓,能夠感受自然的四季變遷。抬頭看見滿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認出星座,銀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樣奔騰。這些當時都沒有想過,但今天作為自然科學專業(yè)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者,這樣的體驗,就是一切的原點吧。”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談及自己為何走上科學之路時,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么會發(fā)光。”應該說,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197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江崎玲于奈有此感悟: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chǎn)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理應無比珍視、精心培育、不斷激勵和呵護。
雖然日本屬于島國,地理條件有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人往往對自己所處的自然環(huán)境懷有一種親近感、自豪感,對各種自然現(xiàn)象也比較敏感。
日本的學校教育也很重視讓兒童親近自然,很多幼兒園和中小學會結合地理條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當?shù)氐淖匀惶厣?/strong>
二、閱讀引領人生成長方向
從幾位獲獎者的言談和著述中,明顯可以感覺到閱讀對于他們成長的重要意義,其中幾位更是因為閱讀而堅定了人生方向。
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學生》一書中坦陳,上小學時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書——愛因斯坦著的《物理學是怎樣產(chǎn)生的》,使他對物理產(chǎn)生極大興趣,并最終走上物理研究之路。
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福井謙一在《直言教育》中寫道:“在我的整個初中、高中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法布爾,他于我可以稱為心靈之師,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從小就有抄書的習慣,他在書中坦陳:“為了讀書寫下很多筆記,并且持續(xù)這種讀書方式,成就了今天在此處的我。”
三、家庭教育注重培養(yǎng)孩子的自立精神如果說閱讀是諾貝爾獲獎者之所以成功的內(nèi)在因素,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則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
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表示,他之所以立志研究化學,就是父親的影響。12歲時,父親帶他參加了一家公司的新產(chǎn)品展示會,新發(fā)布的一種從水、空氣和煤中提煉的黃色尼龍絲讓他覺得“化學實在是太神奇了”,從那以后他的生活已經(jīng)離不開化學。
福井謙一受父親影響?zhàn)B成了刻苦讀書、勤于思考的習慣,他在書中寫道:“至于學習,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態(tài)度,一次也沒有講過‘要好好念書’之類的話。但是,我家卻經(jīng)常籠罩著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學習的嚴肅氣氛。”
與中國一樣,日本歷來重視家庭教育。家庭注重培養(yǎng)孩子的自立精神,從小灌輸不依靠父母的理念。日本學生考上大學后,學費由父母負責,但學費之外的生活費要靠自己打工賺取,否則會受到同學和社會恥笑。小柴昌俊考上東京大學后,第一學期物理全班級倒數(shù)第一,就是過度做家教的結果。
四、大量教育實驗,促進教育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
2014年,日本海亞姆,小朋友們在室內(nèi)游樂場玩耍 / 視覺中國
日本教育與一些東方國家的教育一樣,有灌輸式、重應試等弊病。不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就受到新教育運動、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民間也開展了大量的教育實驗,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教育與現(xiàn)實生活的聯(lián)系。
戰(zhàn)后日本也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吸收了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教育理論與經(jīng)驗。例如,日本的幼兒園、小學并不片面強調(diào)知識傳授,而是特別強調(diào)兒童的生活經(jīng)驗;與基礎教育相比,日本的中學有應試的傾向,曾一度比較嚴重,但高中卻實行學分制,學生有比較大的選課自由。
日本的基礎教育十分重視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很多學校動員近乎全校的教師都參加到課外俱樂部活動指導之的中,甚至有些學生活動(如全國高中棒球賽、全國學生與兒童發(fā)明展等)成為全體國民關心的盛事。
日本也設立一些校外教育機構(如青少年之家等),旨在擴大青少年的視野。企業(yè)也熱衷于舉辦各種科技方面比賽等活動,激發(fā)兒童的創(chuàng)造熱情。而這一切制度或措施都有助于學生形成廣泛的興趣愛好,為未來的事業(yè)發(fā)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覺,而培養(yǎng)這種感性和直覺的最佳時期正是玩得滿身是泥的少年時代。
五、大學科研評價少受急功近利模式影響
專家分析,日本的研究型大學始終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與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日本高校教授在從事科研過程中,自由度也相當高。
在日本,高校老師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nèi)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干擾,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日本人獲諾貝爾獎就是在這種體制下產(chǎn)生的。
日本的科學技術基礎計劃,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參與管理、評審,而是由專業(yè)機構進行。獲得計劃資助的學者,需要認真開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門評定,而是由學術同行評價。
六、視野開闊注重國際交流功不可沒
“日本產(chǎn)生了如此眾多的諾貝爾獲獎者,與日本科學家視野開闊,注重國際交流不無關系。”日本千葉大學經(jīng)濟學博士李仲生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舉例,198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利根川進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他的科學成就都是在美國的實驗室中取得的;200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白川英樹和2001年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國大學進修,均了解各自領域最新的研究動向。
其次,一流的實驗條件為日本科學家提供了堅實的保障。特別是對像物理學、化學、生命科學等非常強調(diào)實驗的學科來說,一流的實驗條件顯得尤為重要,有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的。
2001年野依良治獲獎后,日本政府撥專款7000萬美元為他建立實驗設備先進的研究中心。日本正是憑借其精湛的加工工藝和雄厚的產(chǎn)業(yè)基礎,為科學家進行創(chuàng)新研究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條件。
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能夠取得巨大成就,長期支持其研究的奈良先端科學技術研究生院大學和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功不可沒。 七、科研環(huán)境獨立自由不受干擾是重要原因除了科研環(huán)境的保障,日本科學家始終如一的勤奮刻苦、堅韌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們能在很多領域迅速追趕歐美發(fā)達國家甚至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研究人員自由獨立研究也是研究領域不斷出成果的關鍵。
日本的大學教授和研究所人員申報課題的渠道和形式,實際上是課題注冊制,不必層層審批,一定份額的經(jīng)費就很快撥下來,保障其數(shù)年的研究。
換句話說,獨立自由和不受干擾是日本科學家頻頻獲得諾貝爾獎的主要原因。而日本大學多半是研究型大學,以科研帶動教學,而不是教學型學校,這是日本頻出高質(zhì)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
日本科學家的職業(yè)威望高、工資待遇豐厚也為他們?nèi)闹铝τ诮虒W、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在經(jīng)濟收入方面,日本厚生勞動省“工資結構基本統(tǒng)計調(diào)查”結果顯示,2008年日本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約合90萬元人民幣),大大超過了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八、基礎研究在大學科研中“最受青睞”“上世紀80年代,歐美經(jīng)常指責日本在基礎研究方面搭便車 ,因此日本提出了培育世界水平研究人員的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成功。”《日本經(jīng)濟新聞》指出,“但是,僅靠這些無法擺脫亞洲各國的緊緊追趕。日本有必要培育大量研究人才。”
據(jù)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的論文數(shù)據(jù)顯示,在日本排在最優(yōu)秀大學之后的第二梯隊大學的數(shù)量非常有限,兩極分化的趨勢非常明顯。而在強于基礎研究的歐美各國,這一水平的大學則異常活躍,總體來說,競爭環(huán)境非常激烈。
一般來說,科學技術要轉(zhuǎn)變?yōu)樯a(chǎn)力必須經(jīng)過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開發(fā)研究的漫長過程。但是,日本曾是相對科技后發(fā)國家,為了盡快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它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從開發(fā)研究著手,再向應用研究溯源,最后再深入到基礎研究層面的策略,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日本政府和企業(yè)非常重視對科學研究的經(jīng)費投入,其科研經(jīng)費占GDP的比例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學的研究經(jīng)費雖然在整個科研經(jīng)費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學的研究經(jīng)費的結構與企業(yè)和其他科研機構完全相反,基礎研究經(jīng)費占主要部分(約占55%),而基礎研究正是無限接近諾貝爾獎的溫床。